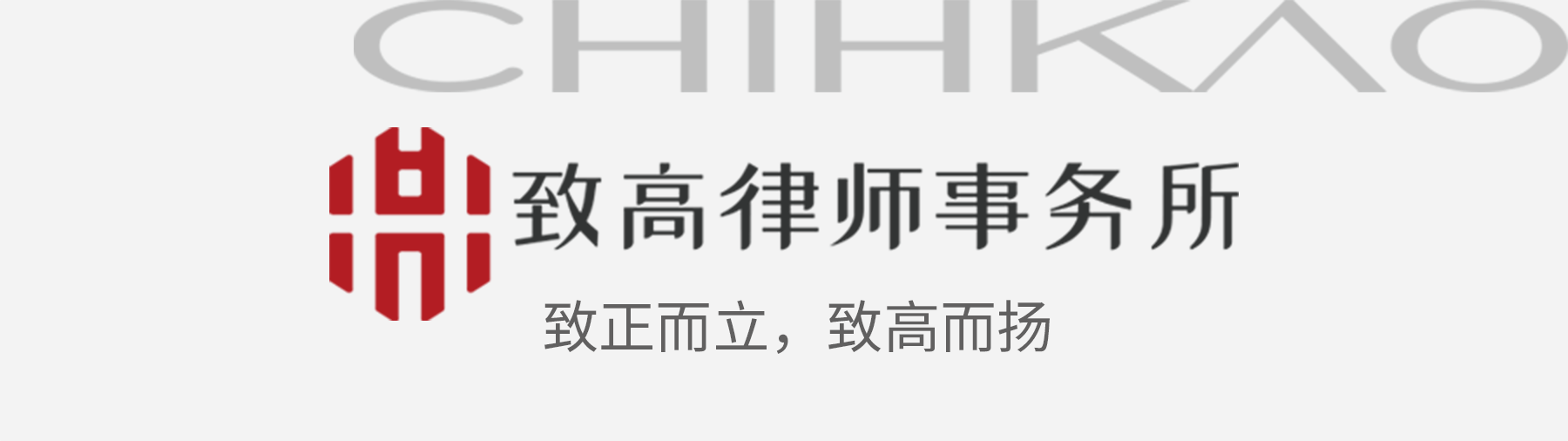
在法律的天平上,我们衡量的是行为与责任;而在人性的深处,真正被压垮的,往往是那些没有站在被告席上的人。
本期“致高律师手记”,徐可欣律师写下了她的看守所会见实录——那里,没有简单的善恶对立,只有现实的沉重、亲情的代价。

这是我第11次来看守所会见他。
跟最开始的意气风发,满怀希望不一样,如今的他一脸颓废,额头上还留着前几天自杀未遂的包扎痕迹。
一般来说,辅警把人送到后会见室便会关门离开,但这一次,辅警特意跟我说:“我们会守在门口,有异常情况请立即呼叫”。
后面的三十分钟会见时间里,他也不再喋喋不休,不再说“我没错,这不应该算犯罪”,说“让我爸妈快想办法把我接回家”,说“你不能帮我做到无罪的话就换个律师,我肯定是无罪的”……
而是几乎全程沉默,只问了一句明知故问的话:“真的没抢救过来吗?”
他问的那个人,是他六十三岁的父亲,是那个拼尽全力四处筹钱帮他退赃退赔试图争取轻判,却因为他咆哮法庭辱骂公诉人,而被当庭宣告我们千辛万苦争取到的减轻处罚不继续适用而当庭痛哭的父亲,是那个庭审结束后回家,却因为精神恍惚导致交通事故身亡的父亲。
法警带他到医院的时候,他父亲已经被“宣告经抢救无效死亡”了。
他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但是,父亲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朋友问,“会觉得他有点可怜吗?”
我说,“不会,他与可怜毫无关联。或许这一次犯罪,是因为他的愚昧而非单纯的恶,但之后的每一次接触,我都感受到了他深扎于内心之处的恶。”
“况且,或许是我冷漠吧,我从不可怜那些几乎无可辩驳的犯罪嫌疑人,哪怕他是我的当事人,哪怕我们总是见面,哪怕我了解了他的过去。真正可怜的,总该是他无辜的家属,以及无辜的受害人跟他的家属。”
或许就像身边同行说的,我是一个十分适合做刑事案件的律师,有同理心却十分清醒,善抓重点且巧言善辩。但其实我自己并不十分喜欢,那种思维上嫉恶怜弱、行为上减罪脱困的极致矛盾和拉扯感,冷眼细看的时候,多少有些茫然和好笑。
“那为什么也还要做刑事案件呢?”
“或许是,生活没办法让人只做喜欢的事情,也要时不时做一些不喜欢却很擅长的事情,才不会让人在舒适区里,沉醉不知前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