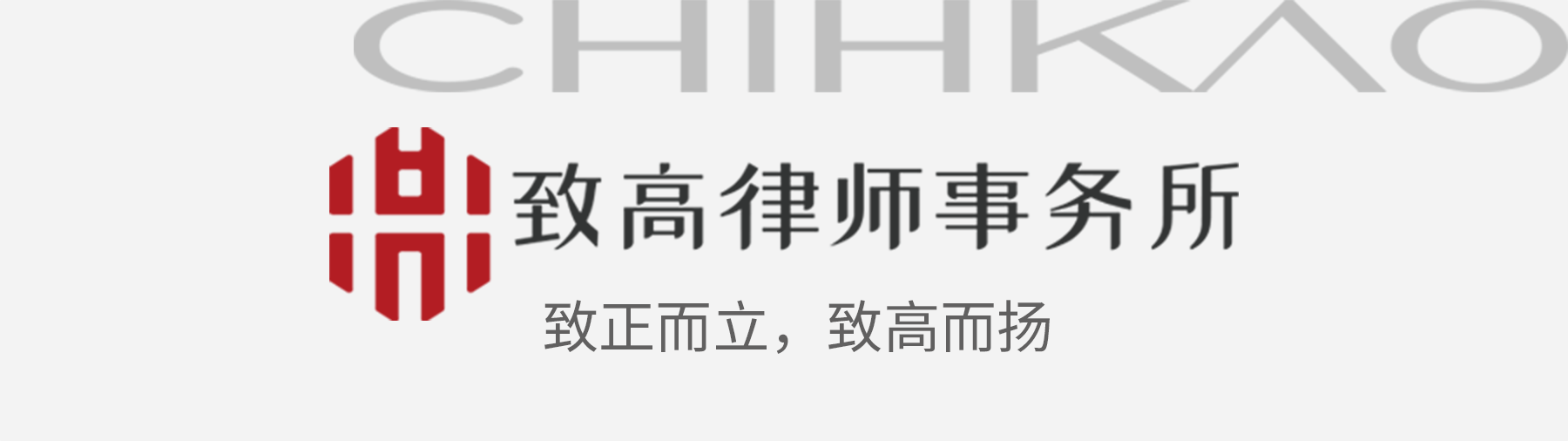公司并购交易中,目标公司财务造假、虚增业绩与对赌协议(估值调整机制)交织,极易触发合同诈骗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与民事欺诈、违约的边界争议。
为系统辨析这一问题,致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范杰律师提出“材料—规则—结论”的分析路径。本文中,他在梳理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规则基础上,分析该领域刑民界分框架:
(1)以是否“实质导致估值调整机制失灵”为对赌场景的关键标尺;
(2)以“履约能力—资金流向—事后行为—证据链闭环”识别非法占有目的;
(3)以“支付对价—扣除真实价值—扣除锁定股份价格—扣除真实收益”的方式评估损失,并指出司法在重大并购案件中对损失口径的分歧。
文章结合公开披露的宁波东力并购年富供应链刑事判决信息及相关学者观点,以“对赌—财务造假—估值”为核心,提出刑民界分的证据化分析框架,以期降低以刑代民与交易风险外溢。

并购交易中的“欺诈”何以走向刑事?
并购交易以信息与估值为核心。对价通常基于财务报表、业务合同、客户集中度、应收应付结构、税务合规等信息形成。若目标公司通过虚构合同、虚增收入利润、隐瞒重大亏损等方式影响估值并促成交易,可能构成民法典意义上的欺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亦可能在满足非法占有目的等要件时,落入合同诈骗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评价范围。
典型案例中,上市公司宁波东力并购年富供应链后触发刑事追诉。公开公告披露,该案以合同诈骗罪追责并涉及并购对价款、增资款等损失。该类案件往往同时呈现“交易结构复杂、对赌安排存在、尽调与评估介入、事后经营恶化或暴雷”的组合特征,使刑民界分更需证据化、规则化。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基本界限
(一)罪名与关键构成
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当然从“财务造假”推定,而需结合履约能力、行为方式、资金去向与事后表现综合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2号,已失效)中列举了利用合同诈骗的典型情形,并以“明知无履行能力仍签约骗取财物”等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判断线索。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时间与证据要求
检察机关研究明确指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不应扩张为“事后”产生的故意;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并避免仅以损失结果客观归罪。在“借鸡生蛋”式融资周转情形下,如资金确用于经营且存在支付对价之意,一般不宜轻率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三)民事欺诈与撤销路径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作出意思表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该救济强调交易纠偏与利益返还,并不当然指向刑事追责。刑事评价应以对交易秩序与财产安全的法益侵害达到一定程度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

对赌协议的特殊性:以“估值调整机制是否失灵”为关键标尺
对赌协议(估值调整机制)在并购中用于分配不确定性风险:一方以业绩承诺、补偿、回购等方式对未来收益作出安排,另一方以对价或股权锁定承担风险。
清华大学周光权教授指出,对赌协议的本质是估值调整,纠纷原则上应优先在民事领域解决。即便存在造假行为,如果估值调整机制未失灵、投资人在对赌期内兑现收益或补偿、且行为人具有补偿能力与意愿,不宜轻率认定合同诈骗。
相反,当行为人在估值时造假,使估值严重脱离交易价值,或在对赌期内持续虚增业绩导致对赌安排沦为空文,进而使投资人陷入错误处分财产,才可能成立合同诈骗。
由此可将“是否实质导致估值调整机制失灵”作为识别是否就重要事项实施欺骗、以及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指标。

“刑民界限”的审查节点
可将并购欺诈的刑民界分落实到四组审查节点:
1.履约能力:并购前是否已资不抵债、核心业务是否真实可持续、是否存在系统性虚构合同、应收款、是否具备对赌补偿能力。
2.资金流向:并购对价、增资款、借款、担保利益是否被抽逃、转移、挥霍或回流;是否存在以并购名义套现并迅速脱手的安排。
3.关键虚假事实是否决定交易:虚假事实是否集中在估值关键变量(收入、利润、应收账款、重大合同、核心客户)并对定价与对赌条款产生决定性影响。
4. 事后行为与风险隔离:是否积极纠偏、补偿、披露;还是隐匿真相、伪造资料、继续虚增以拖延对赌期并实现解锁、套现。
上述节点的意义在于:把抽象的“非法占有目的”转化为可举证、可反证的事实,并为法院在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层面提供可操作的审查路径。

损失认定:并购型合同诈骗案件的难点与分歧
损失认定决定定罪量刑与追赃挽损。周光权教授提出的路径具有较强解释力:应从投资人支付的对价中扣除目标企业真实价值;对尚在对赌期内的案件,还应扣除锁定股份价格;投资方在对赌期内获得的真实收益亦应扣除。即所谓“实质性损失”,避免把商业风险一概刑事化。
但在重大并购刑案中,司法对损失的审查可能更为严格。以宁波东力并购年富供应链案为例,公开披露信息显示法院在犯罪金额认定中纳入并购对价款、增资款及担保所致损失等,体现出对“整体交易损害”的评价路径。
该分歧提示:并购型案件应强化对目标公司真实价值、锁定股份市值与投资收益的证据化计算,以免损失被单向放大。

结论:用“证据说事”替代“标签化定性”
第一,并购欺诈的刑民界分,应当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并以履约能力、资金去向、关键虚假事实对交易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对赌机制是否失灵为主要审查轴。
第二,对赌协议并非天然“刑事化”。在对赌补偿可实现、投资方可通过民事路径纠偏的场景,应坚持刑法谦抑性,避免以刑代民。
第三,建议在审判与办案中强化损失证据的技术化审查:真实价值评估、股份锁定与解锁收益、现金流折现等应形成可复核的证据链,并明确区分“商业风险损失”与“欺诈导致的实质损失”。
第四,交易参与方应从合规与证据留存层面前置防控:尽调底稿、评估假设、核心合同与客户验证、对赌触发与补偿路径、资金流向监控与信息披露机制,均应作为“未来争议中的证据资产”管理。